头号书迷(外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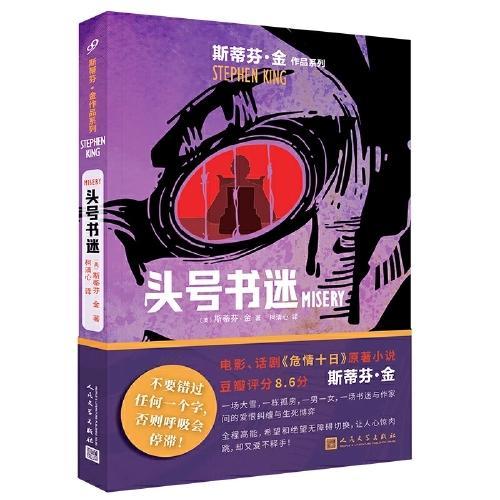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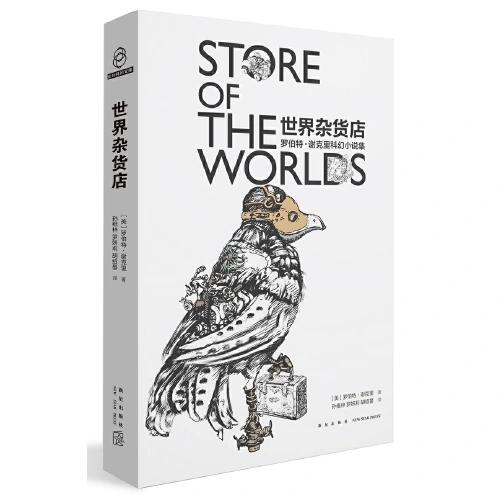
□李万华
读到一种说法,斯蒂芬·金写小说《米泽丽》(中文翻译《头号书迷》),是对疯狂书迷所作的一个答复:1986年,因为常年受不到美国主流文坛的认可,斯蒂芬·金宣布放弃恐怖小说创作,转向科幻小说创作,消息一出,“金迷”誓死反对,坚决不从,于是斯蒂芬·金写下这篇小说,作为应答。
小说中,作家保罗的书迷安妮·威尔克斯是一位退休护士,早年曾数度犯下命案,却每次都巧妙逃脱法律惩处。安妮收集保罗的每一本书,熟读它们,迷恋书中人物,与他们共悲喜同荣辱,同时她也寻章摘句,用书中的语句来应对现实,譬如“有一种审判凌驾于人类之上,我会由他来裁决。”无疑,作为读者,安妮虽不聪明,但绝对忠实。安妮对保罗的痴迷不仅仅拘囿于书本,她还像侦探那样,从书籍中挖掘作者的所思所想,搜集来自作者自身的每一丝信息。她熟知作者的写作习惯、兴趣爱好,她甚至追踪作者形迹,窥探作者的生活隐私。作为书迷,安妮是疯狂的。作者遇到如此穷追猛打的书迷,算不上是一种幸运,偏偏安妮是精神有问题的那一种。她身材臃肿,喜怒无常,她心细如发,冷酷强悍。她强迫作者烧掉新作,只因为她不喜欢书中粗言秽语,她怜惜书中人物,以砍掉双足的方式来摧残被她囚禁的作者,只为了让作者将书中人物复活。
斯蒂芬·金也够疯狂,塑造一个如此歇斯底里的书迷来回应自己的书迷。
然而斯蒂芬·金在《写作这回事:创作生涯回忆录》中,谈到《头号书迷》时说,小说的雏形仅仅来自一个飞机上的梦,而且安妮·威尔克斯根本另有所指:
“我内心深处的一部分早在1975年就知道我酗酒,我那时写了《闪灵》。作为作家的我不肯接受这一点。而知道我在酗酒那一部分的我决不甘心沉默。它用自己唯一了解的方法,借小说和角色之口大声求救。在1985年后半年到1986年初,我写了《米泽丽》(这题目很恰当地描述了我当时的心态),小说中有位作家受到一个精神病护士的囚禁与折磨。”
“我确实想了——尽我当时的混沌脑袋之所能——使我最终下定决心的是安妮·威尔克斯,《米泽丽》里那个神经病护士。安妮就是可卡因和酒精,我认定自己已经厌倦被安妮奴役,为她写作。我担心自己戒酒戒毒以后无法再写作,但我决定(我在筋疲力尽、极端抑郁的状态下,只能做出这么点决定),我如果别无选择,宁肯放弃写作,也要保住婚姻与家庭,看着孩子们长大成人。”
似乎是误解与真相的问题。
至于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斯蒂芬·金在《写作这回事:创作生涯回忆录》中另有阐释:
“那么,我们假设你现在就在自己最钟爱的接收位置,而我待在发送信息的最佳地点。我们跨越空间,还要跨越时间,才能完成这次精神交流。这其实不是个问题。我们如果能够阅读狄更斯、莎士比亚,以及希罗多德(也许要借助一两个脚注),我认为我们也能够跨越从1997年到2000年这么点距离。那么,我们开始吧——真正的心电感应正在发生。注意,我袖子里没藏什么东西,嘴唇也没动过。你很可能也毫无动作。”
而当我看完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危情十日》(又名《头号书迷》)时,浮现出作者与读者的另一种关系:
有时候,作者是一位射箭手,手握一把弓,一束箭。他(她)引弓,一箭击中目标。那目标也是读者想击中的,可是读者技能欠缺。读者只好看着目标击中处涟漪泛起,朵朵白花,只好载歌载舞,艳羡喟叹。有时,读者不小心沦为目标,被箭射中,疼痛不已。如果读者脾气暴躁,会勃然发怒。大多时候,读者会隐忍,会分身,他(她)会将疼痛的那部分挪去当别人,另一部分则躲在一边云淡风轻。
就是说,有时候读者也是一位射箭手。
成为一只猫
皮德是格罗姆星球上的一位飞行者,这次他的任务是带领两位属下到另一个星球去放置瞬间转移器。物质瞬移器是格罗姆星球上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它能让物质在任意连接的两点间实现瞬间转移。就是说,只要瞬移器安置成功,一启动,格罗姆星球上过剩的千军万马就可以瞬间转移到他现在要去的星球上。这既节省移动的能量,又快速,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皮德属于飞行者种姓,这种种姓的形体更适合开飞船。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曾祖父,乃至他的所有先辈都属于飞行者。他们沉默寡言,生生世世都在飞船上。
格罗姆人会变形,这是他们特有的能力。他们的形体既可以变作其他事物,也可以液体般流动。不过,格罗姆星球并不安定,许多人对自己的种姓形态不满意。譬如,采矿者种姓不满意自己固定不变的采矿者形态,想要有所改变,但这一种姓在采矿出现时已经确定,几万年的形体,说改变就改变是一种罪恶。许多人对自己种姓不满意的另一个原因是,种姓有高低贵贱之分,采矿者属于低级种姓,飞行者属于高级种姓。
为了安置瞬移器,格罗姆星球先后派出了二十支探险队,可每支队都有去无回,不知所终,现在,皮德带领第二十一支小队前去一探究竟。
比起只有八种动物形态的格罗姆星,那个蓝色星球上的物种形形色色、五花八门。遗憾的是,那个星球上的人类有着固定不变的形体,他们自始至终保持一个模样,不能挑剔。那个星球就是地球。
这是罗伯特·谢克里的小说《形态》的开始部分。故事的结尾,同去地球的三个格罗姆人,一个变成了地球上的一棵橡树,他喜欢站在飒飒的风声中思考,一个变成了地球上的一只狗,它跟着另一只狗跑进森林去捕猎,捕猎是他喜欢的事情。他俩都不喜欢格罗姆人到地球上毁掉地球的一切。坚持到最后的皮德,安置瞬移器即将成功的时候,忍不住走到窗前,瞅了一眼窗外的世界,然后,他飞身跃出——“窗外,窗外有一只雪白的巨鸟,它展翅高飞,尽管有点笨拙,但还是在越来越有力地追赶远处那群鸟类。”
这可以是一篇关于背叛的小说,也可以是一篇关于自由的小说,有关形态自由的权利。
以前,我总是说,想成为一只猫。我说这句话时毫不费力,觉得这是我的真实想法。然而当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的猫蹲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地盯着我,它的眼神充满期待,甚至是一种哀求,它“嗯嗯啊啊”地叫,意思是要我放下手里的东西跟它玩。它每次都这样,清早醒来就开始闹着要和我玩,躲猫猫,掷皮球,或者逗猫棒,都行,它对玩的内容不挑剔,只要跟它玩就行。可我总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的事情琐碎无比,一件件相连,没完没了,我不能花一个早晨或一整天跟一只猫玩。于是每次猫咪如此恳求我时,我便敷衍它玩几分钟,或者打发它自己玩。可它玩不了几分钟又来找我,原因无非是,它的乒乓球跳进了沙发缝里,皮球滚到了床底下,兔毛玩具也不知去了哪里,或者,它就是要和我一起玩。
除了睡觉,除了捉一只飞到玻璃上的虫子,除了跳起来玩一下猫旋,除了追尾巴,它总是要跟在我身后,小孩子似的,可以跟一天,跟一夜,夜以继日地跟。而这样的黏人,换作我,是无法做到的。我在骨子里是一个独行侠,我做任何事情只要有时间陪伴就行。
譬如此刻,这初秋的薄暮,我收拾完厨房去外面走走。院里的李子已经绯红,香荚蒾的红果开始变黑,灰头鹀的宝宝胆子太大,每天都在同一棵杏树下觅食,而那棵杏树旁边的人家养了两只猫,窗户总是大开,黑猫蹲在窗框上,橘猫在猫架上睡觉。如果出门,一排槐树秀气地站在行道旁,树下的八宝景天开出浅紫的花。再往远一些,白蜡树在风中静立,空气中飘来烧烤的味道,烤羊肉,烤鱿鱼,辣椒油加孜然加花椒粉。如果我走进一家名叫“果小蔬”的蔬果店,可以买一盒蓝莓或一斤无花果。无花果新鲜,果皮上的紫色有点像八宝景天的花。拎着水果往回走,头顶的树梢上,是一片幽深的天,月亮有时有,有时躲到楼后。
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切实地,从功能的角度想到猫的形态受限太多,根本无法完成诸如买一斤无花果这样的事情。当初我说成为一只猫,只是因为我跟大多数不是宠物的猫相似,喜欢离群索居,独来独往。现在想,“成为一只猫”这话过于宽泛,应该加个前缀,“成为一只独来独往的猫”,并且仅仅是灵魂方面的,形体上,我终究舍不得放弃人身的自由。
确实如此的,这尘世中没有任何一种自由是完全的自由,这一种自由的得来首先需要牺牲掉另一种自由。两者不能兼得,彼此无法平衡的道理很早就懂了,就是忍不住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糊涂。
编辑:祁进梅;